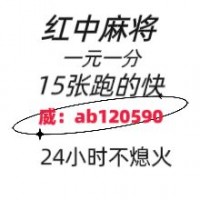功夫的长歌当哭浅唱在北风的时节里,现在回顾犹如凉风袭来,掺杂着宁静的气味动摇着本影的树枝,落叶笔直的飘荡归溯着一曲善感陈腐的乐律,细数凄凉的风韵,犹如冰封已久的时间,一种莫名的憧憬涌上心头,在安之素若里消失喧闹的背地,在人命的薄凉的曲途,想起咱们的故事,从发端到中断就像空中楼阁一律的扑朔迷离,蔚为大观
静庐,一个静字,多像一位归隐于街市的隐者,这才是真正的大隐
现在,我们不妨看一眼这座私家宅院中主人一天的生活: 五更将尽的时候,一声鸡鸣唤醒了仍在沉睡中的小镇,有微弱的亮光开始从苍山顶上朦朦胧胧漾出,分辨不清是天色还是苍山顶上积雪的白色
某间屋子里传出非常细碎的悉悉索索声,稍后不久,声音略微大点的开门声“吱呀”一下划过深深的庭院,于是从井里打水、往地上泼水和扫地的声音小心翼翼而又紧张忙碌地交响起来
毫无疑问,这才是刚刚开始的序曲,音乐的转换处,一个男人的咳嗽声像定音鼓一样略微有些沉重地传出,这让两个还想赖在床上多躺一会的小丫鬟像两个音符一般一跃而起,三两把就穿上了衣服,一边出门还在一边系上白族女人特有的风花雪月帽子的系带
一个丫鬟急急忙忙用银质脸盆去灶间打已经温热的洗脸水,而另一个则用细碎的步子奔进二楼的上房,于是,上房的几扇窗子立即就有蜡烛的红光流淌出来,紧接着,中院之中几乎所有的门扉和窗户次地打开
有狗在汪汪的叫,她瞥见一只口角花的小狗激动的跑来,见它跑的呼哧呼哧的,张着嘴吐着舌头,东跑一圈西跑一圈
瞥见她歪着头汪汪汪的叫着,阿婆听出来了,它是在和她打款待,它痛快的摇摇尾巴
有松塔被风摇落,掉在它头顶,吓它一跳,便对着松塔汪汪叫着表露它的果敢
一看它不动,就走近用鼻子闻闻没啥滋味,又用右爪趴拉扒拉看没啥伤害,还辗转翻滚的和松塔玩上了,遽然立起一只耷拉的耳朵听到主人的召唤,像小兔子一律赶快的跑远了
黄土高原上,陕西关中西北部地区的麦客,在关中麦子成熟时,大量涌入关中受雇割麦
这种情景,据说已延续了三四百年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麦客”这个名字,会叫我们联想起“侠客”、“黑客”来,挟裹着一股子豪爽的江湖气
麦客们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也像行走江湖的艺人,不过出卖的是力气罢了
他们随身携带着几件换洗旧衣,还有炒面干粮,镰刀是工作的利器
他们行走在田间山道上,风餐露宿,像迁徙的候鸟,个中辛酸滋味,谁能体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联合收割机介入了麦客的行列,机械化的抢占,并没有赶走手工的麦客
他们的战场是收割机派不上用场的山坡地叉,边边角角
已故摄影家侯登科,跟踪拍摄了麦客的生活历程,视角朴素沉重,溶入了悲悯情怀
有一幅照片,画面上的麦客是个中年汉子,额上是刀刻剑凿的皱纹,他穿着破旧的衣衫,汗流满面
他正搭着一条腿,拿镰刀用力勾起一抱焦干的麦子
看着他,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的神情专注——专注得发“木”,这“木”是过度的劳累所造成
在这里,不需要任何思维想象,也没有丝毫的诗意,太阳的光芒,毒且辣,实实在在地灸烤大地
这儿需要的只是体力和耐力,麦客们也只有这两样东西
十、想一万次,不如去做一次
奢侈的摔倒,超过无谓的徜徉,任何不痛快的时间全是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