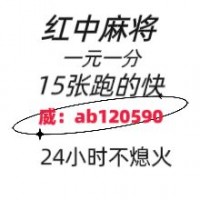跳蚤在人身上、羊毛狗毛里躲藏着,时时布满杀机
在这山里,低矮的木楞房上面是人住的,下面就是羊厩,他们的家就是跳蚤的家
而我是它们无意中寻找到的一个新的家园
无处不在的跳蚤,让我想起了久违的虱子和臭虫
在我的学生时代,昏暗脏乱的学生集体宿舍中,欢笑和喧嚣的下面掩藏着成团的虱子和白色的虱卵,躺在床上一仰头看到的是蚊帐角落里红黑色的臭虫挤成一团
一想起这些在贫穷中最容易见到的东西,虱子和臭虫让我感到恶心想吐,而眼前的跳蚤让我感到恐怖
面对生的忧患,他俩宁愿遁入首阳山采集野菜,咀嚼大自然的英华,充当历史王道中的英雄角色,也不愿随波逐流
百年以后的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讲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如此大忧大患和伯夷叔齐的“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的忧虑和不归相比,简直如出一辙
难怪同为儒家学范的他们,要被后世立为历史王道里的道德标向
在哲学意义上讲,“无用性”标志着肉身与精神的彻底断裂
信念、理想抑或希望一旦陷入“无用”,那么,精神的生命又将何复以求呢?虚无的深渊,绝望的深渊是真正的归宿
《圣经》中有亚伯拉罕的绝望,约伯的绝望,耶酥的绝望,而伯夷叔齐的绝望就是宁可“饿且死”,亦不归
信念欠缺乃至于对人世的欠缺的认识,把伯夷叔齐逼上绝路
登上首阳山,也就意味着对自己精神的反叛和放逐
屈原有《天问》,高士有《采薇》
一个投江,一个饿死
尽管选择的方式不同,但求道无门时的解脱却极其相似
体面地与那个格格不入的世界告别,其实也是希冀在冥冥的逍遥之中得到拯救,一种内心的拯救,和信念的拯救
“他愈嚼,就愈皱眉,直着脖子咽了几咽,倒哇地一
8、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
是的,我很少对我的出生地的名称抱有好感
从小镇的车站下车,一抬脚就进入了普枫的地界,我总是低着头默默地走到村子里去
那个村庄与村庄连在一起的地方,来来往往的人群,根本就与虚无中的普照寺和枫树形成了明了的对照
青黄色的泥土路上,村人推着两轮车,上面装载着饲料、粮食、农药,进村出村,都显得很沉稳
从学校里刚放学回家的学生们,骑着自行车,在阳光里向着家里飞窜,周杰伦一样的打扮,说明他们经常能够从电视里看到时代的舞步
扬尘而过的农用车、轿车,使留在村里的人和离开了村庄的人,把村庄支撑着,成为远近四方丝毫不逊色的富裕之地
我,一个像男孩的女孩,遇到妨碍时会像大气的男孩儿把货色埋在内心径自一人接受这不公的十足
但当我再没辙负载这深沉、惨苦的事...
前几天遇到一个朋友,她惊讶地说:“你脸上的那一对脚印呢?”我自豪地说:“春天都走了,留她做什么,被我彻底铲除了,以后不许在我脸上兴风作浪
”她笑着说:“你的肤色很好啊!”我也善于做自我表扬,我说:“女人的脸色就是心情的标签
”那一刻,走在春天的阳光里,内心被小小的幸福感淹没了
谁知我的快乐还没有延续上一周,谁料到孩子又过敏了,孩子的过敏几乎带给了我抗击过敏成功带来的所有快乐
小学时的徐姓女生,我们玩在一起,等我上中学的时候,她已回家务农,临别她依依不舍的送我一个塑料皮日记本,我则把一个蝴蝶发夹别在她的头上,我们都流下眼泪
之后的一年,我有回家机会,总要抽出时间跟她见上一面
记不起这段友谊的消逝过程,只是慢慢的彼此无了音信
我们离的不远,8里村路算不上沧海桑田,没有特别的借口刻意设计相遇,我们几乎20年没有见面,在江湖中忘的太久,越发的无话可说
学会追回并回头看,首先你必须有一个目标,它不需要象征峰值,只要你超越自己,即使是一小步,我认为你不是一个优秀的中学生,至少我不会追逐我只失去它,我会珍惜它,我一直这样,珍惜一段时间,将落在路上
揉揉了惺松的睡眼,第一件事就是找那只蝴蝶
找来找出,也没看见它在蚊帐上,把被单撩起,发现了蝶儿,它没有变成美丽的仙娘,却死在了我的枕旁
我不领会,从什么功夫发端你就如许走进了我的内心
纵然我很不想去供认,就算我能捉弄世界人,可我捉弄不了我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