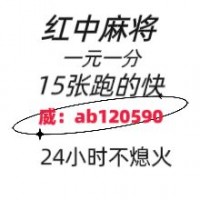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
贝多芬故居在莱茵河西岸大桥下波恩大街20号
门口挂着用德文花字体写的“贝多芬故居”的一块牌子
庭院里的手压抽水机、酿制葡萄酒的工具和盛酒的大木桶,都保持了当年的风貌
哦,我记起来了
是有这么一回事
那女孩还附了一张照片给我,是个有一双大眼睛、一头刘慧芳式秀发的漂亮女孩,散文写得很棒的
抗日阵亡将士墓立着新旧两块墓碑
新碑取材黑色花岗岩,横嵌于墓正壁,满版金黄色的字简述着雀尾战斗概况和墓的重修过程
旧碑取材青石板,直嵌在新碑左侧,横额写着“功在党国”四个大字,碑文为:陆军第十六师第四七团于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在诸暨应店街抗日之役担任掩护之阵亡将士:林学烈、陈老桭、王长兴(碑中25人)等九十四名之墓
陆军十六师四十七团团长石补天敬立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
从落款时间看,这一抗日墓碑距今已77年历史
这是一只狗,伤痛的、隐忍的一年
但愿秋风很快照拂我窗前的植物,但愿花盆里的软泥很快弥合我足下的创伤
22、情人节出租:逛街10元,穿情侣装20元,在空间上秀恩爱25,接吻30
(小本生意不讲价)
这个逻辑应该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文学不是谁谁的专有,不是一块某个人家里的铺设和装饰,她应该会在恰当的时候垂青走近她的人,例如某些时候的我,以及其他的人、灵魂、歌者甚至是普通的凡人
可就是这一句话,也许是江湖版本的太多,有了歧义,于是两位女人下山了
昨天黄昏,我第一次在表面过华诞,很欣喜,有一群伙伴,伯仲,在我身边,很痛快
《站在夜晚的风中》是永亮的第二本诗集,他的第一本诗集《长笛手和他的旧歌》,我也有幸早于许多人先行阅读了
在读《站在夜晚的风中》中时,有许多东西在我的心里激荡着,汹涌着,奔突着,我知道,我要说些什么了
有一个词叫如鲠在喉,读永亮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我就有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
我和永亮的相识和友谊要上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其时我们还是两名洋溢着稚气的中学生,那一年我读初三,那是1988年,对于中国的文坛和诗坛,那是最热闹,也是最有活力的年份
先锋小说家和先锋诗人们,用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风暴
而永亮和我,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被一种巨大的力量裹挟着懵懵懂懂地走进了文学
那个时候我们俩像极了两头对世界满是好奇的小鹿,就象本能地热爱青草一样,我们身不由已地热爱上了诗歌
其实确切一点说,永亮的写作要比我早一些,大概是始于1987年,或者还早
但1988年对于我个人来说,它的确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异常重要的一个年份
因为我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写作,并且结识了当时就已经才华横溢的永亮兄,永亮是个全才,他不仅文学功底扎实写出了大量的优秀诗歌,而且他的音乐天赋,他的美术造诣,他的硬笔书法作品……在当时的校园中就颇为周围的人们所称道
他的绘画在中学生绘画竞赛中得过一等奖,他的画评总是道常人所未道;他的书法飘逸潇洒,矫若游龙;他后来干过长笛手,吹过小号,在部队的军乐团待过,而我最看重的,却还是永亮的诗歌,也正是因为诗歌,我和永亮开始惺惺相惜,并很快成为了最好的诗歌朋友
1988年或者那以后的几年中,我是永亮家中的常客,永亮的哥哥宋永照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诗人,也因为这个原因,永亮家中的藏书甚为丰富,我每次到永亮家中除了和永亮谈诗歌,就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那是我以前从未涉足过的真正的文学的海洋
在永亮的家中我读到了《诗刊》、《诗神》、《诗歌报》等这些中国一流的诗歌期刊,也是在永亮的家中我知道了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欧阳江河、昌耀、于坚、韩东、海子、西川、陈东东、李亚伟、周伦佑等等这些中国诗坛上非常耀眼的名字
也是因为永亮,我得以认识了当时在诸城现代诗歌写作最前卫的青年诗人韩宗夫
而我后来的写作得益于永亮和宗夫甚多,应该说是他们让我对诗歌有了一个不同于当时的教科书的全新的认识,我也由此少走了很多弯路
是永亮和宗夫让我一开始就接触到了现代诗歌最本质也是最内核的那种东西,这为我的以后的写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从文学的意义上,我的内心对永亮和宗夫是充满了由衷的感激的,如果当年没有永亮和宗夫的引领,或许我至今仍然停留在浅薄的汪国真式的写作上,或者徘徊在文学之外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情,就是永亮和我都曾经当过兵
我们都有过当兵的经历,而且我们两个都主持过曾经颇有些影响的“含羞草”诗社,编过30余期的《含羞草》诗刊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含羞草》已经成了联系我和永亮友谊的最重要的一条纽带
要说我和永亮间的诗歌缘分,《含羞草》是一个不能不说一说的名字
一个文学社团,一份油印刊物,永亮入伍之前,类似托孤般地将他主持并任社长多年的《含羞草》诗社移交给正在读高二的我
当时永亮对我的为人和我的诗歌写作水平的信任,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他眼里透出的热切的光辉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当然后来我也幸不辱命,《含羞草》在我主持时期在诸城二中乃至整个诸城都影响深远,社刊也由最初的油印改为打印
《含羞草》社员也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后来的近百人
如今,对于永亮和我来说,《含羞草》已经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也是最重要的诗歌记忆之一
应该说是这份叫《含羞草》的油印或者铅印的诗歌刊物,营养并成就了我和永亮,日后很多年过去了,受过《含羞草》影响的人们肯定还会记着《含羞草》这个名字,记着曾经编过《含羞草》的两个诗歌青年:宋永亮和韩宗宝
缘于此,今天当我面对永亮的第二本集子,我内心的感慨和感触是难以言表的
作为永亮的诗歌兄弟,作为永亮十几年写作的见证者,就目前摆在我面前的这本收入了永亮1992年到1996年间创作的所有诗歌作品的《站在夜晚的风中》,我不揣浅陋地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或者认识
在诗歌中,或者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永亮都保持着一种低调的姿态
但也正是他的低调和谦卑,赢得了朋友们的更高的赞赏和期许
他写爱情的《伤》、《十月·十四行诗》,前者是写美丽情怀,而后者更多地写到了内心的悲凉;写军旅的《今年的春天》、《兄弟》、《老兵王全保》等等,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让我感到分外亲切,特别是《兄弟》一诗,写于1992年,却具有了某种很强也很难得的理性的色彩;而诗歌《老槐》背后的隐喻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他所写的绝不仅仅是一棵槐树,而是写时代和人们观念的一种碰撞;他在《蝶》中所展示的语言才华以及总体上浑然天成的《天空的颜色》,让我们感觉到了一个心地纯净的永亮;而《风啊风啊》中他所表达的那种难言的痛楚,和在《意想不到的冬天》中他的那种无话可说的隐痛,是一脉相承的
我认为永亮诗歌中对语言和内心的观照最为典型的还是他的著名的《与菊花相依》,他在诗中这样写到:“望见雨撞击岩石,/雪花落进火焰,/乌鸦飞出黑夜
/望见一个人燃起火把,/火把照亮十一月的天空,/望见天空逐渐黯淡,/人们呀,/我看见了黯色中的菊丛”
《与菊花相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为语言的炼金术士的诗人宋永亮
他带着调侃写《多年未谋面的一位同学》、《看见甲与乙》,诗中的描述令我们会心而笑
在《母亲从乡下来》中他写那种难言的疼痛
《多收了500斤》中他写农民的无奈,对丰收的失望,诗歌中那种隐约的反讽,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多收了三五斗》
在《熟人》中他让生活本身说话
组诗《画家》中他对几类画家的刻画栩栩如生,可谓入骨三分,生动地营造出了反讽的艺术效果
《情人》对款爷的深刻讽刺,击中他们的软肋
而《拜访某局局长》则不动声色地实现了对某一类人的嘲弄,进而对伪善的人性给予了无情的揭露
很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从平常的生活中发掘诗意
众所周知,处理日常生活往往是一个出力不讨的好事,一些有经验的诗人在写作中总是有意识地避开这类题材,因为平常的生活很难提炼出诗意
而永亮却一直努力用诗歌表达着他置身其中的生活,他的这样努力也获得了应有的回报
那些充满了生活气息的优秀的反映现实的诗篇,就是诗神对他的最高奖赏
相比之下,我认为他1996年写下的更加接近诗歌本身,更能呈现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品性和良知
诗歌不仅要技巧,还要对生活的爱
他诗歌中的讽刺和愤怒,缘于他对生活的强烈的爱,没有鲜明的爱,就不会有鲜明的憎
他在诗中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某些现象某些人的憎恶和不屑,而这正是一个诗人在目前这个物欲时代必须保持的节操
永亮是一个爱憎分明的诗人,也是一个崇尚真善美的诗人,对虚假和丑恶,他在诗中总是进行无情的揭示和批剥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应该做的
诗人,我以为诗人不应该过多地写咖啡,酒吧,红地毯,夜莺,玫瑰,等等,而是要关注生活,特别是底层的生活
真正优秀的诗歌应该是扎根于社会的底层的,但真正的诗歌绝不是所谓的“为人民歌唱”,而是扑下身子踏踏实实地“作为人民而歌唱”
这是一种写作姿态
哔竟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是十多亿的农民构成了我们国家人口的巨大基底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去掉了农民,中国还能剩下什么
说到底,一个作家或者诗人,他的写作能否为人民所认同,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是不是站在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最大多数人的立场上
很多年里,永亮一直在底层生活,这对永亮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诗歌是一种人格力量,通过永亮的诗歌,完全可以折射出他的人品
在永亮的身上有一种让人钦佩的东西,也正是这种东西,在山东诸城以永亮和他的诗歌为中心,周围聚拢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优秀的文学朋友
1996年,对于宋永亮写作已经日臻成熟,在创作上他也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理论体系
我们不难看出,在永亮这一年的诗歌写作中,技巧和语言,已经退到了第二位
他写于这一年的长诗《1996:心灵备忘录》,是他隐忍了多年的才情的一次大爆发
读这首诗时,我真正地感到了那种来自心灵的力量
请我们记住这些诗句:“是铁,/还是即将腐朽的楠木
/深入一九九六年的冬天,/我掩面而泣,/却不用悲愤
”,“人们抛弃的河岸长满了荆树,/涉水而过的人,/重新捂住自己的伤疤
”,“主啊!/请埋葬我最后的罪恶,/用你无可匹敌的大水,/击碎仅存的一块船板
”,“犀利的刀锋也不落在纸上,/让自己隐藏于一个中性的词中,/星辰退去,/他在设想的草原上步步为营
”
应该说这首诗的完成,是永亮在1996年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同时也意味着他今后的诗歌,必将会有一个新的标高
由于这首诗,我对永亮的诗歌开始有了更深更高的阅读期待
和《1996:心灵备忘录》不同,同样写于这一年份的诗歌《生活片断(之五)》,则异常真实地凸现了永亮个人的日常生活
我能读懂那种窘迫
或许除了我,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理解永亮
生存,多年来就如一条大毒蛇,紧紧地纠缠着他,让他始终不能抬起头来,从容地行走
但可贵的是在诗歌中他始终是坦然而平静的
是一种来源于心灵的力量,让他的诗歌具备了一种足以抵抗生存压力和人生风雨的力量和品格
他是人群中行色匆匆的那个人,一脸生活的疲惫和真诚
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他酷爱辣椒,越辣越好
我想他只所有如此喜欢这两样东西,大约借助香烟和辣椒能缓解,或者冲淡生活中的苦味
很久以来,他也喜爱饮酒,但我很少看见他喝醉,酒后的他往往出现两种状态,一是保持沉默,沉默的可怕!二是遇见志同道合的文友,就会滔滔不绝的谈论作品,如果谁要在酒后窥见永亮对某人作品的真实评价,最好是在这种状态
他自嘲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他说从未发表过诗歌,但他写下的诗歌比目前许多刊物上的诗歌,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语言上都要优秀的多得多!他不是一个看重发表的诗人,他所注重的是对自己诗艺的悉心打磨
十多年来,他在诗歌中步步为营
他一点一点地,慢慢地靠近着诗歌
客观一点说,永亮的诗歌,目前仍然是人们所谓的“抽屉中的诗歌”
他绝少投稿,到目前为止,十几年来大约投过一两次稿
诗歌是一种慢,这在永亮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并且深刻
而正是靠他的大量的未发表过的优秀的诗歌作品,永亮赢得了圈内朋友们的一致赞赏和尊敬,这对于那些急功近利,挖空心思炒作自己,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们来说,是颇有一些讽刺意味的
诗人最重要的还是要靠扎扎实实的作品说话
在作品之外下的所有的功夫,都是浅薄甚至可笑的
韩宗夫是永亮和我都十分尊敬的一个诗人,有一次当被人问及为什么总是在生活中沉默时,他曾说过这样一句很有意味的话:我沉默是为了让诗歌更好地发言
应该说永亮是秉承了宗夫的这种重要的诗人的内在品质的
最近以来,由于网络的缘故,永亮的部分诗歌开始散布在一些诗歌网站上
他的诗歌正在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影响,一些著名的诗人,如马永波、汤养宗、王夫刚、岩鹰、格式等,对永亮的诗歌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这些年来我虽然发表过一些作品,但当我面对永亮,面对永亮的诗歌,我还是很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差距和浅薄
从这个意义上,我对永亮充满了敬意
永亮已经沉默了十几年,除了有限的几个朋友,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诗名,在全国,提起宋永亮这个名字,肯定没有几个人会知道,但我相信,有一天,宋永亮这个名字一定会让整个中国诗坛感到吃惊的!因为他的沉默已经让他蓄积了足够的力量
而如果你能有幸读到这本编年体的,1992-1996这五年间永亮写下的《站在夜晚的风中》,我相信当你读完这些诗歌之后,你一定会记住这个叫宋永亮的诗人!1996年永亮写下的好诗有很多,比如《兴华西路》、《指导员·李》、《小号演奏者》、《朋友》、《日记:十月二十九日,苏鼎、韩宗宝来我家小聚》等等,限于篇幅就不具体说我的感受了,相信聪明的读者会比我更能理解并领会这些诗歌
其实永亮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他还是一个优秀的诗歌评论家,永亮的评论总能让人洞悉并触及诗歌背后和诗歌深层的那种东西
他对诗歌的理解、把握和解读,常常是十分精到而深刻的
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永亮的许多诗评,甚至比所评的诗歌还要耐读
当然这就已经是题外的话了
本来我对诗歌的认识十分有限,对一个人和他的诗歌指手画脚,更非智者所为,但因为永亮是我最好的诗歌朋友,一说起来就收不住了
竟然,拉拉杂杂地写了数千字之多
我自己知道,我所说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废话
好在永亮兄不介意,并且温和而大度地容忍了我的浅陋和呱噪
这多少给了我一点点自尊
前面所谓如鲠在喉,不过是一个说话和写文章的幌子
但以上的文字的确是我读完永亮的第二本诗集后,最想要说的一些话
现在终于说完了,我也就应该识趣地闭上我的不怎么让人喜欢的“尊口”
哔竟,一个喋喋不休的人是令人讨厌的
“这样的时代,诗人适合做一个哑巴
”永亮似乎说过类似的话
我想今后,我更多地是要向沉默中的永亮学习:面对诗歌,背对名利
做一个令人尊敬的“时代的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