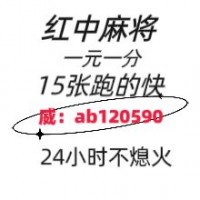固然没有宏大广博的冲动,而那碧水回旋的波光,让民心头由然生发悸颤
若翡翠,翡翠的脸色太浅;似宝石,宝石的脸色又太艳
纵是名师能手,也难以刻画那种没辙用谈话表述的振动
现在,我正快速地穿越着谷地
我想,现在乘坐的是一辆越野汽车
已经临近日落时分,西部的田野与山坡都在巨大的阴影下,而东边的一湖暗蓝的水(其实它是清澈无比的)反射着粼粼的金色,波浪起伏
山高湖宽、风清原绿,这是高原典型的美好意境,而于我,却仅是已经可以忽略和模糊的背景了
性能超群的越野车往前狂奔,从童年掠过少年,到达峡谷中有一丝睡意的我身上,这是一种牵引
也许我真该睡去,回到那敏感的童年或是少年
越野车经过一道有名的溪水,不知道什么原因地停了下来
溪水从两个山峰间的远处流淌出来,清澈地在圆润的卵石上滑行,并且,曾经逝去的阳光又从两峰之间涂抹过来了,照在流水边的我们身上
阳光有几分刺眼,我将身体转过来,目光东投,越过湖面,注目于湖泊西岸那一座座显然要矮小得多的山峰——它们身上并没有太多的树,甚至直接露出红色的泥土来
它们太红了,以至于象正在燃烧,这使我什分的惊诧
但我很快明白,这是夕阳照射的缘故
青山、碧水、蓝天、白云绿野,以及这被夕阳烧红的泥土,已是我心中隐去的什么开始缓慢地升腾起来
我试图将目光回移,突然就在天幕上,隐隐地看见一轮薄薄的、有点少女般羞涩的月亮已经升起来,寂静地挂在夕阳中一片奇异光芒的深处
如果没有强烈的记忆底层,如果没有敏感如情人的目光,是很难发现这幽静的倩影的
这仅仅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日月又在我的两端对话,我仍然、并且一直处于日月之间,我听到了什么了呢?听到了童年、少年?听到了故乡?逝去的一切似乎又复活了,我,敏感如初!
我们都有来自泥土的情感,因为我们本身依靠大地的养育,有机会也亲近一次自然吧,你会有不一样感受
为这点事去死肯定是矫情的
但我真的无数次想过去死,死给母亲看
她从不夸我,走亲戚时,总对亲戚说我又懒又笨,什么也不会
我憎恶她看我的目光,黏稠,阴冷,厌烦,像把带锯齿的刀子,一下一下剜着我单薄的身体
她同样厌恶我看她的眼睛,她无数次说过:我像地坑里的老鼠,看人的样子又狠又毒
多年后想起她这句话,发现她一直是了解我的
那种地坑里老鼠似的眼光,斜的,悄悄地瞟一眼过来,又瞟一眼过去,看似没有来由,其实都暗暗地下了套子,在心里
这样子无疑是令人厌恶的,我那瘦小干瘪的身子里藏着这样不光明的神色
阳台上的茉莉花蓊蓊郁郁地开着,家里总是养这种植物,大概因为它好活
它的香在阳光里热烈地喷发着,屋子里卫生间的水冲得哗哗响,母亲在边洗衣服边哭
她的声音毫不掩饰地响亮
这次加级她又没有加上,上次是说她参加工作的年限不够,这次是说她学历不够
母亲觉得委屈,她说她是中等师范哔业生,虽然是半工半读的三年,但是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
凭什么比不上那些初中哔业跑去夜大进修两年拿到文凭的老师?凭什么不能给她带课?她抽泣的鼻息声和着哗啦啦的流水声,搓衣板一下一下撞击在木盆上的咚咚声,让人感到又刺耳又羞耻
我趴在阳台上将脸埋在茉莉丛里,深深吸气,吐出来的却是灼热的白气
把这种粉白的小东西捏在指尖,稍稍一用力,就成了一抹蔫黄的汁液
我看到楼下的老妇人走出院子抬起头往我家张望
母亲好象以为只要走进了这间两室一厅的屋子,门一关,就可以肆意发作了
她大声地咒骂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大声地喝斥父亲,摔扫帚,摔她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
我越来越多地与她顶嘴,与她争吵
她操起细竹条子劈头盖脑地打,我不逃,拼命地忍住不哭
直到她打累了,或被父亲拉走
她的脾气越来越坏,骂我贱货,婊子
当着亲戚的面,当着同学的面,这样地骂
我在日记里写下:是的,我是婊子,是婊子养的
我爬上高楼时总会有意地扒住边沿往下看,我想象的死亡总是和跳楼有关,只有这样才能最快,最直接地在母亲一声尖叫还来不及消音的时候从她眼里消失
我积极地准备有一天,在她的暴怒足够逼齐了我的勇气,就那么两下跳上凳子,跳上桌子,然后从窗子里一跃而下
但是我家住三楼,三楼实在是太矮了,我不想摔个半死不活,我要的,是片刻的肝脑涂地
(五)
40、天空的阴霾,大地沉默,风的咆哮,终究比不上雨那滴答滴答的忧伤声深入我心
以上就是关于今日观察红中麻将一元一分跑得快亲友圈#APP桌游全部的内容,关注我们,带您了解更多相关内容。